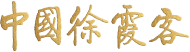[36]载《消暍集》。
[37]载《定峰诗钞》卷五,民国三十四年甲戌江阴陶社版,见台湾新文丰出版社《丛书集成续编》第173册。
[38]载《民谱》卷五十三《盘水坝原标河南第十七世贡士仲昭公传》。
[39]载《江上诗钞》卷四十九。
[40]载毛晋《和友人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册。
[41]载《确庵文稿》卷二。
[42]载《第十世隐君退庵公传》,见《民谱》卷五十三。
[43]载张洪《梅雪轩序》,见《民谱》卷五十七。
[44]载黄暘《梅雪轩序》,见《民谱》卷五十七。
[45]载敦本堂《袁氏宗谱》卷三袁一义世系表。
[46]载明代张佳图著《江阴节义略》“许用”条,见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第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7]载《暨阳许氏宗谱》。
[48]载《(光绪)江阴县志》卷十六。
[49]关于沈鼎科的死,目前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本文所说自缢,出自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又见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的《明代传记丛刊》收录的《复社姓氏传略》卷三。另一种出自《(乾隆)江阴县志》卷十七沈鼎科传:“会流寇犯阙,明帝宾天,鼎科呕血成疾,乙酉夏避难山野,遂卒,年四十一。”
[50]载《漫水第十六世宗门士杰公传》,见《民谱》卷五十三。
[51]以上引用内容出自《民谱》卷五十八,与徐华根编《明末江阴守城纪事》收录的《义城赋》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