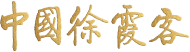袁枚《子不语·徐崖客》的学术意义
陈锡良
袁枚有篇《徐崖客》
清代,江南有位从官场退休的著名文人袁枚,原籍浙江杭州,中晚年长期定居南京城内随园,人称随园老人。他著作丰富,有册文言笔记小说集《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其中有篇《徐崖客》,主人翁徐崖客的故事和明代历史人物徐霞客的事迹有惊人的相通之处。赏析这篇《徐崖客》,对于研究徐霞客颇有些价值。此文不长,转录如下:
湖州徐崖客者,孽子也。其父惑继母言,欲置之死。崖客逃,云游四方,凡名山大川,深岩绝涧,必攀援而上,以为本当死之人,无所畏。登雁荡山,不得上,晚无投宿处,旁一僧目之曰:“子好游乎?”崖客曰:“然。”僧曰:“吾少时亦有此癖。遇异人授一皮囊,夜寝其中,风雨、虎、蛇虺,俱不能害。又与缠足布一匹,长五丈,或过高,投以布便攀援而上。即或倾跌,但手不释布紧握之,坠亦无伤。以此游遍海内。今老矣,倦鸟知返还,请以二物赠公。”徐拜谢别去。嗣后登高临深,颇得如意。入滇南,出青蛉河外千余里,迷道,砂砾渺茫,投囊野宿。月下闻有人溲于皮囊上者,声如潮涌。偷目之,则大毛人,方目钩鼻,两牙出牙牙颐外数尺,长倍数人。又闻沙上兽蹄杂沓,如万群獐兔被逐狂奔者。俄而大风自西南起,腥不可耐,乃蟒蛇从空中过,驱群兽而行,长数十丈,头若车轮,徐惕息噤声而伏。天明出囊,见蛇过处,两旁草木皆焦,己独无恙。饥无乞食处,望前村有烟起者,奔往。见二毛人并坐,旁置镬焖芋甚香。徐疑即月下遗溲者,跪而再拜,毛人不知,哀乞求饥,亦不知。然色态甚和,睨徐而笑。徐乃以手指口,又指其腹,毛人笑愈甚,哑哑有声,响震林谷。若解意者,赠以二芋。徐得果腹,留半芋归。视诸人,乃白石也。徐游戏遍四海,仍归湖州。尝告人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凡草莽幽绝之所,人不到者,鬼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处,便有人矣。”
袁枚笔下徐崖客的原型就是徐霞客
袁枚笔下的“徐崖客”和历史人物徐霞客事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首先是姓名相似:江南一带“崖”“霞”读音相同(读作“呀”),字形不同,实质同类,都是自然界景物。袁枚生前,民间传说中的徐霞客喜好游历名山大川,在口口相传中误会或附会成攀崖登岭的“崖客”,也不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两人登雁荡山的情节神似:都攀援浙江名山雁荡山;在攀援中都得到老僧指点和资助,都使用重要工具——缠足布。只不过徐霞客所用是两个随行仆人的,而徐崖客用的是老和尚所赠。
再次是两人都曾游历西南边陲:
其中第一,两人都遭遇过巨蟒。徐霞客经常深入猛兽出没的险境,旅途中多次绝粮,探险中数次遭遇生命危险。在深入探索广西真仙岩洞中,徐霞客目睹巨大的蟒蛇横卧石隙间,没有受到伤害。徐崖客滇南游时,野宿时伏在皮囊里,遭遇“长数十丈”、“头若车轮”、“腥不可耐”的巨大蟒蛇驱赶着“万群獐兔”的恐怖情景,也没有受到伤害。他俩都遭遇巨蟒,只是袁枚对徐崖客遭遇巨蟒作了极度夸张的描述。
第二,两人都目睹过“毛人”。毛人,就是传说中的介于巨猿和人类之间的类人动物,俗称毛人、野人。野人身材比人高大,披发毛身,毛色多为棕红,无尾,直立行走,奔跑如飞,力大无穷。许多方志文献都有类似记载。例如,屈原的《九歌·山鬼》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写到这种类人动物。湖北《房县志》:“房山高险幽远,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啮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徐霞客《滇游日记》记载有“腾越之西,则在红毛野人。”仅此一句,就非常珍贵,是研究古今生态变化的重要资料。徐霞客有没有见过野人?笔者认为,徐霞客长期出没深山密林,完全有可能见过野人。钱谦益所撰《徐霞客传》中,不啻写见到野人,还写与野人作伴:徐霞客“……以岩为床席,以溪涧为饮沐,以山魅、木客、王孙、(jue,决)父为伴侣……”山魅,传说中的山鬼;木客,传说中高居于树上的似人非人的怪兽,实际上山魅、木客就是野人;王孙,猴子的别称;(jue,决)父,马猴,大型的猴子。徐霞客即使没有目击到野人,至少会从当地见过野人的百姓中采访到有关野人的信息,而且徐霞客以其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对野人必有相当的认识。否则,当本地百姓把当时还过着原始社会生活的“茶山之彝”也称为野人时,徐霞客就不会认为“茶山之彝”不是真正的野人,而是“昔亦内属,今非王化所及矣。”
袁枚笔下的徐崖客所见野人,身材高大(夜间在徐崖客的皮囊上小便,“声如潮涌”),能笑能发声,但不会说话,这样的描写符合野人特征。但是,袁枚又写它们能使用火,能使用人类工具(“置镬焖芋”),又不符合野人智能习性。所以,撇开“方目钩鼻,两牙出牙牙颐外数尺,长倍数人”近乎荒诞的描写,袁枚笔下的野人只是夸张的文学形象,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实动物。除了《徐崖客》,袁枚在《子不语》里还有多篇写野人的故事,说明野人不像鬼怪、狐仙那样纯属虚构,而有可能客观存在。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袁枚笔下的“徐崖客”的原型,就是徐霞客。
袁枚通过哪些可能的途径了解徐霞客
《徐霞客游记》最早的刊本,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徐霞客族孙徐镇所刊,刊本开始只能在社会上小范围流传。享年82岁的袁枚当时61岁,《子不语》里不少篇名是用了历史真名的,像曹操、张飞、王莽、陈子昂、柳如是等。笔者估计袁枚当时没有见过《徐霞客游记》刊本,否则他就不会把江阴徐霞客写成“湖州徐崖客”。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五年赞扬徐霞客《溯江纪源》很有价值,估计袁枚对此“圣谕”也不会知道。袁枚不可能看到《四库全书》中的《徐霞客游记》以及杨名时两篇《徐霞客游记序》。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在乾隆三十八年才开始编纂,历9年成书。乾隆十三年袁枚就辞官定居南京。《四库全书》仅抄七套,原抄四套,分别珍藏于北方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和文溯阁,续抄三套分别珍藏于南方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虽是士绅却是平民的袁枚不会有资格去翻阅。《四库全书》直到1796年嘉庆元年才有数量有限的刊刻本行世,而袁枚在1797年就去世了。因此他只能在民间传说中了解徐霞客的一些事迹。
徐霞客多次到邻省浙江旅游考察,湖州、嘉兴、宁波、台州、绍兴、温州、衢州等地都到过,接触过许多文人、和尚、道士、市民、农民,游浙次数及景点之多、考察程度之深,接触人员之广,除了云南,是其它省份所不及的,因而他在浙江官方、民间能成为口口相传的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传奇式人物。他28岁时初探雁荡湖,20年后47岁时二探、三探雁荡湖,其情节本身的完整性、惊险性,是会被传得神乎其神。这是袁枚写《徐崖客》获取素材的社会基础。
袁枚是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他聪明早慧,12岁入县学,24岁中进士,至少在24岁前是一直在浙江生活、读书的。他热爱大自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对于百年内流传于浙江一带的徐霞客(徐崖客)故事,肯定会有所耳闻。
袁枚对徐霞客事迹更多的了解,当在他做官以及辞官以后。袁枚考中进士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散馆后在江苏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四县知县,贤能爱民,政绩甚佳,深得百姓爱戴。然而他生性疏淡,虽身居庙堂,却心系山林,33岁就辞去官职,提前退休。65岁以后,袁枚开始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的黄山、江西庐山以及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都有他的足迹。 在游历中袁枚完全有可能听到关于徐霞客传奇色彩的故事。旅游中的见闻,亲朋好友的述说,都会成为他创作的素材。袁枚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加以想像夸张,便塑造出笔记小说《徐崖客》来。袁枚自己在《子不语》序言中就这样写:“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
《子不语》的写作特色
《子不语》是笔记小说集,专记鬼神怪异之事,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合称清代三大志怪小说集。鲁迅曾精辟评价《子不语》:“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袁枚以徐霞客旅游探险为基调写《徐崖客》,而两人的家庭身世竟大相径庭:徐崖客不是江苏江阴人,而是浙江湖州人;徐崖客母亲不是生母,不是贤明豁达、疼爱儿子的贤妇,而是继母,是欲置继子于死地的恶妇;徐崖客不是孝子,而是孽子。如果历史上真有徐崖客这样的身世和骇人的游历,地方志会以重要的隐逸人物加以记载,然而笔者查阅《湖州府志》及所属县志,都没有看到记载,说明湖州历史上没有这个传奇人物。这就印证了袁枚所说“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这种笔记小说的笔法。可见鲁迅说袁枚写作“率意”是恰当的。因为是笔记小说,所以袁枚没有也不必去考证真伪。诚如鲁迅谈到小说创作手法时所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者听过的缘由,但决不会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至此,或许有读者会说,袁枚笔下的徐崖客根本不是徐霞客。笔者要回答:只有了解了笔记小说的特点,才能肯定徐崖客的原型就是徐霞客,没有徐霞客就没有《徐崖客》。
《徐崖客》的学术意义
笔者解析袁枚《子不语·徐崖客》,认为至少有两点学术意义。
第一点,雁过留声,虎过留迹。袁枚《子不语·徐崖客》的出现,可说明现代称之为“地理学家和旅行探险家”、古代称之为“隐逸人物”的徐霞客,他的事迹,至少在他在世及身后至清代中期乾隆年间,就不只在官方、而且在民间,早已广为流传的了。
第二点,《徐霞客游记》和《子不语》都写到野人(《子不语》有多篇写野人),还有许多其他典籍记载有野人,这为现代有没有野人的自然生态变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野人、外星人和飞碟是当今世界之谜。当今中外科学界承认古代有野人,而当代是否有野人则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野人早已绝迹,一种认为野人还残存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神农架群众多例目击野人出没的报告,中国科学院至少组织了3次有规模的野外科学考察。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1977年,中科院和武汉部队、当地政府及民间人士组成110多人的联合考察队,在神农架搜寻野人,没有取得突破。其后不少民间人士发扬徐霞客的探险精神,深入神农架原始森林,探寻野人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和部分科学家在理论上认为:巨猿和大熊猫在远古共生共荣;沧海桑田,现在大熊猫在国内原始森林里还残存着,巨猿的后裔——野人,理应存在着;根据古籍记载,根据当代目击传闻,人类的近亲——野人还残存着。
笔者赞成野人还残存的观点,而且认为,如果现在能发现真正的野人(或活体或尸体或头骨),其科学意义决不会亚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必将引起世界关注。
(作者系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