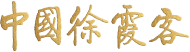

徐霞客“独造雁山绝顶”考
蔡崇武
徐霞客之挚友陈函辉说:“徐霞客曾‘三游台宕’、‘四游雁宕’。”经过考证后,陈函辉说的“三游台宕”已经被证实,“四游雁宕”中,其“三游雁宕”,已包含在“三游台宕”中(见本人《徐霞客首游天台、雁宕之考辩》、《徐学研究》2024/4)。徐霞客“独造雁山绝顶”之游,在其“四游雁宕”中目前乃本人唯一不曾予以考辩之篇章。虽然,已有多名徐学专家进行过探讨,但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我并不赞同,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原则,我深感到很有必要谈一谈我的一些观点,以求得徐学界朋友的指正。
一
徐霞客“独造雁山绝顶”,并非是一篇单独的游记,它只是陈函辉与徐霞客见面吃饭时,陈函辉问徐霞客一句:“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徐霞客听了,顿时心动,就在“次日”,单独上了雁山之巅,完成了一次独立的雁山绝顶之游。这件事,只有在陈函辉的《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有所记述。原文是这样的:“予席上问霞客:‘君普一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听而色动。次日,天未晓,携双不借叩余卧榻外曰:‘予且再往,归当语卿’。过十日,霞客来,言:‘吾已取间道,扪萝上。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冢也。再攀磴往,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两僧团瓢尚在。又复二十里许而立其巅,罡风逼人,有麋鹿数百群,夜绕予宿。予三宿而始下山。’”陈函辉听了徐霞客的介绍,十分感慨地道:“其果敢直前如此。”赞叹不已。
由上述记述可见,徐霞客这次“独造雁巅”真实可信。陈函辉和徐霞客是挚友,据泰州周娴先生在《我爱徐霞客》一文中记述,徐霞客是通过徐仲昭其父徐文光而认识陈函辉,当时徐仲昭的父亲徐文光为浙江“海宁训导”,而徐仲昭与徐霞客是亲戚,从而通过徐文光的介绍而结识陈函辉。因此,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当徐仲昭委托陈函辉为徐霞客起草《墓志铭》时,陈函辉欣然接受,其原因是“然辉(陈函辉)与先生交最久,义不敢以不敏辞。”这里的“交最久”,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两人何时相识相交,但相互结识的时间肯定是很长久了。但“久至何时”,文中没有交待,是否像周娴先生说是的1613年,即徐霞客写作《游天台山日记·浙江台州府》时就相识相交,这有待进一步考定。但从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的记载看,徐母王孺人1625年去世之事,他是知道的,而且对徐霞客从其母亲去世,到服阙的事情的记述十分详尽,这可以证明那时,即1625年起,陈函辉与徐霞客的交往已经十分密切。因此,两人相识一定在1625年之前,至于究竟确切的时间是哪一年,还可以继续探讨。
虽然,根据历史考证,可以证明,徐霞客与陈函辉在1625年前就相识相交,但那时,徐霞客还在“服阙”期间。按照中国古代的规矩,晚辈在“服阙”守孝期间是不可以有任何游艺活动的。而“服阙”需要三年,也就是说,徐母王孺人是1625年去世的,在1625-1627这三年间,徐霞客必须在家守孝服阙,不可能去登山游历,据丁文江先生在《霞客徐先生年谱》中记载,也确实如此,徐霞客当时在家“服阙”三年,因此,徐霞客在1628年才重新开始游历,故而,即使徐霞客真如陈函辉记载的那样去“独造雁巅”,也必定是在1628年及以后的事。最迟是1632年,因为丁文江先生认为,徐霞客与徐仲昭一起游览天台山和雁宕山最后一次,就在1632年;而靖江高峰先生认为徐霞客“独上雁巅”,是徐霞客“四上雁宕”的最后一次,即在徐霞客与徐仲昭游过天台、雁岩之后的1632年7月。再则,我们必须关注到,从1628年到1632年这五年中,据丁文江先生的《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记述,1629年徐霞客游京师,这一年肯定未去浙江。1631年,徐霞客家居,未外出旅游。这样,徐霞客“独上雁巅”,只有可能在1628、1630和1632年这三年中,因为,这三年据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记载,徐霞客均到过浙江。
二
陈函辉似乎出了三个谜题,但这三个谜题,其实并不是“谜”,因为陈函辉在鼓动徐霞客“独上雁巅”并在徐霞客上了雁巅之后,就在与此同时,他和徐仲昭碰了头。徐仲昭是徐霞客的族兄,大徐霞客6岁,他对徐霞客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当他听到陈函辉介绍了徐霞客“独上雁巅”之后,并没有惊奇,相反,当场发表了一通议论,而正是这一议论,为我们解开了徐霞客“独上雁巅”之谜。
徐仲昭这样对陈函辉说:“仲昭笑曰:此咫尺地(指徐霞客“独上雁巅”)何难?记入燕,陈明卿与言崆峒广成子所居,其上可窥塞外。霞客裹三日粮竟行,返即告明卿以所未有。不数日虏已抵蓟门矣!自江上走闽,访石斋于墓次;又为赍手柬抵粤,登罗浮,携山中梅树归。次年,追石斋于云阳道上。犹忆余在西陵,霞客从曹娥江独走四明,五日,赤足提朱兰来,夸我‘以山心石窗之胜。’吾弟之信心独往,无所顾忌,而复不轻为然诺,皆此类也。”——详诸先生叙赞中(见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霞客游记》诸绍唐、吴应寿整理,1194页)。
徐仲昭这段话极为重要,它至少表明了下述三个问题:一是说明徐霞客不畏艰险,独立探险,是徐霞客特有的习惯。徐仲昭是知情人,他例举了徐霞客一系列探险的实践。如徐霞客千里迢迢赴燕探险塞外;赍手柬抵粤,登罗浮,携山中梅树归;从曹娥江独走四明,赤足提朱兰来。从而说明徐霞客“独上雁巅”这是他一贯不畏艰险的特点。而且用“携山中梅树归”和“赤足提朱兰来”,说明这是徐霞客“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乐观豁达的秉性。从而告诉读者,徐霞客“独上雁巅”一事,绝对真实可信。二是徐仲昭在叙述中,两次提及徐霞客与黄道周的交往。一次是1628年访石斋于墓次,一次是1630年初“追石斋于云阳道上”。徐仲昭在这里反复提黄道周(即石斋),实际上说明徐霞客十分尊重贤者,从而曲折地表明徐霞客同样十分尊重陈函辉。他答应陈函辉“独上雁巅”绝非戏言,他说到做到,表现了他一诺千金的优秀品格。三是徐仲昭的一席话,非常重要,他否定了两个事实。一个是徐霞客1628年“独上雁巅”的可能性。据徐仲昭的回忆,徐霞客“赍手柬抵粤,登罗浮,携山中梅树归。”这一年,就是1628年。徐仲昭的回忆,徐霞客这一年到达了福建、广东,而且登上了罗浮山,为母亲去世求各个知己、朋友题“秋圃晨机图”。得到了题词后,就“携山中梅树归”,也即回到了江阴。这一切,徐仲昭就是个见证人。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同样记载道:“是年先生游闽,南至罗浮。”还到过漳州,见过族叔徐日升。不仅如此,还访黄道周(石斋)于漳浦墓次。最后远赴广东等地,请求各地贤者,为逝去的母亲题《秋圃晨机图》。为题词徐霞客不辞辛劳一一拜访,据丁文江记载,这一年,求得题词者有何楷、张燮等十多人。在众多题词到手后,据丁文江先生记述,他“归途则取道兴化、泉州。”更重要的是徐仲昭这段话是讲给陈函辉听的,如果在1628年徐霞客与陈函辉碰过头,徐仲昭不可能不提及,相反,徐仲昭讲到1628年的有关事端后,又接下去讲了徐霞客1628年以后的行踪,一直到1630年初徐霞客与黄道周再次碰头的事例,这充分说明,徐霞客经过浙江与陈函辉碰头,只可能在1630年的下半年,徐霞客“独上雁巅”,也只能在1630年的下半年。
另一个是,否定了1632年徐霞客“独上雁巅”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其一,徐仲昭和陈函辉的对话,证明了徐霞客“独上雁巅”,在1630年,不可能在1632年。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徐仲昭叙述的徐霞客与黄道周第二次会见的事。徐仲昭从徐霞客“入燕”讲起,一直讲到1630年“追石斋及于云阳道上。”这是1630年年初的事,徐仲昭讲到这里为止,这充分说明当时陈函辉与徐仲昭谈论徐霞客“独上雁巅”一事,就是1630年下半年的事。如果徐霞客“独上雁巅”发生在1632年下半年,那么,1632年上半年徐仲昭与徐霞客刚刚一起游过天台与雁宕,不会一字不提。更重要的是,那次徐霞客与徐仲昭同游雁宕时,在山顶曾遇到“骇鹿数十头也”,这是陈函辉知道的。为何在徐霞客“独上雁巅”,见到“有麋鹿数百群”,陈函辉还显得惊喜异常,称“其果敢直前如此”!仿佛第一次听到山顶有麋鹿之事?因此,足见徐霞客“独上雁巅”是比徐霞客与徐仲昭“三游台宕”更早的事,也就是1630年的事。其二,著名的徐学专家丁文江先生,对徐霞客“独上雁巅”也发表了看法,他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写道:“陈(函辉)记载:‘壬申(1632年)秋以三游台宕,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按先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初游台、宕,故是年三月为第二次”。观陈志似先生秋间曾再赴台者,然墓志又言:“予席上问霞客‘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听色动。”次日,天未晓,携双不借叩予卧榻外曰:“予且再往,归当语卿!”过十则霞客来,言:“吾已取间道扪萝上。上龙湫三十里,有岩焉,雁所冢也,……有麋鹿数百群,夜绕予宿。”而游记载先生于三月二十日自天台再游雁宕,四月十五日返天台。四月二十八日达黄岩,三游雁宕。五月三日上雁湖,四日由大龙湫登绝顶,遇骇鹿数十头。……这里丁文江先生清楚地表明徐霞客“独上雁巅”,为徐霞客“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初游台宕”后的“第二次”游雁宕。虽然丁文江先生只是说“故是年三月为第二次”,未能交代“第二次”为何年之事,但肯定是比“四月二十八日达黄岩,三游雁宕”要早得多。这已十分清晰地表明,丁文江的判断,徐霞客“独上雁巅”,是在徐霞客与徐仲昭1613年第一次游台、宕后,但绝对在1632年第三次游台、宕之前。虽然,丁文江先生并不知道,1612年徐霞客曾首游天台、雁宕,但他能坚持认为徐霞客“独上雁巅”是在徐霞客与徐仲昭1613年游过天台、雁宕之后和1632年游天台、雁宕之前,即他所说的“第二次”(实为第三次上雁宕),这实属了不起的历史成就,值得充分肯定。如果丁文江先生知道1612年徐霞客曾独上天台、雁宕,那么,他必定也判断此次徐霞客“独上雁巅”为第三次,这就和我的观点完全一致了。因此,虽然徐霞客“独上雁巅”未在徐学界引起广泛讨论,但从目前已有的资料可资证明,徐霞客这次“独上雁巅”是一次独立特行的活动,时间应在1630年,是在“四游雁宕”中的第三次。这一点,上述众多资料已足可证明。
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靖江高峰先生忽视了这些事实,他在《侧身回望台雁峰——徐霞客四上雁宕考》一文(见《徐学研究》2024/1,34页—37页)中,充分肯定了陈函辉提出的徐霞客曾“三游台、宕”和“四上雁、宕”,这是在徐学研究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的。但在具体解读徐霞客“四上雁宕”时,却不能令人信服,有了随意性。他把徐霞客在《游天台山日记(后)》中的一段话:“三月二十日,抵天台县,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乃尽天台以西之胜,”作为徐霞客“二游雁宕”的证据,这是依据不足的。我在《徐霞客首游天台、雁宕之考辩》一文中已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把这段嵌在徐霞客《游天台山日记(后)》中的一段话,作为单独上雁宕之游来看待是不当的。这里,我不想对此多作议论,只想对高峰先生把陈函辉记载的徐霞客“独上雁巅”,作为徐霞客“四游雁宕”来看待,发表一点不同看法。
高峰先生认为:陈函辉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记载的徐霞客“独上雁巅”,是徐霞客“四上雁巅”,即第四次上雁巅。他在《侧身回望台雁峰——徐霞客四上雁宕考》(见《徐学研究》2024/1总第六十九期)中推出了徐霞客三上雁宕之后,写道:“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上旬徐霞客的大致行踪。月初,徐霞客与徐遵汤到小寒山与陈函辉‘烧灯夜话’,而后四上雁宕,返回临海,与陈函辉相晤。返程经杭州与郭浚交游。十五日至苏州与黄道周同游太湖。”这里,高峰先生十分明确,徐霞客那次“独上雁宕”是第四次上雁宕,是在“七月中上旬”,时间是在与陈函辉“烧灯夜话”之后。正因为高峰先生把徐霞客“独上雁宕”说成是徐霞客在1632年七月中上旬的一次单独的四上雁宕旅游,因此,他把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推断徐霞客那次“独上雁宕”为“是年三月为第二次”的推想,大批特批,认为丁的推论是错误的,“后人出于对其信服,往往不加辨别,加以援引,遂为定论”(见《侧身回望台雁峰——徐霞客四上雁宕考》)。高先生的观点,虽然仿佛是无可辩驳的定论,其实,只是根据自己的臆断,值得商榷。
高峰先生把徐霞客“独上雁巅”说成是“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中上旬”,他在《侧身回望台雁峰——徐霞客四上雁宕考》一文中写道“月初(指1632年7月),徐霞客与徐遵汤到小寒山与陈函辉烧灯夜话,而后四上雁宕,返回临海与陈函辉相晤。返程与郭浚交游。十五日至苏州,与黄道周同游太湖”。为了证明徐霞客“独上雁巅”是“四上雁宕”,他摆出了两个论据:一个是徐霞客的朋友郭浚的一首诗。他说郭浚在他的《虹映堂诗集》卷五有一首诗,题作《徐霞客游台雁归赠以长句》,正是作于崇祯五年秋,徐霞客四游雁宕后,返程经过杭州之时。这里,高峰先生是明显搞错了,郭浚写得很清楚,这是他在《徐霞客游台雁归赠以长句》,也就是说,是在徐霞客1632年3月起游了天台山和雁宕山回来以后赠以长句,而不是徐霞客“独上雁巅”后赠以长句,郭浚不仅在诗的题目中指出了写这首诗的由头,是有感于徐霞客游了台雁,有所感触而写了这首诗,决不是为徐霞客“独上雁巅”而写。而且,郭浚诗的前言里也作了说明,他写道:“壬申秋孟,复游台雁,还与予遇西子湖,出陈木叔赠诗读之。”郭浚说得明明白白,写这首诗是因为“壬申秋孟”,徐霞客在千申年三月到五月间“复游台雁”后,还与予遇西子湖,徐霞客“出陈木叔诗”读之,从而有感而发,写作了这首诗。这里郭浚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写这首诗,是因为徐霞客“复游台雁”(即游了天台山和雁宕山之后)有感而写。这里的“复游”,说明郭浚只知道徐霞客第二次游天台山和雁宕山,根本没有提及徐霞客“独上雁巅”之事,从诗的前言来看,是符合郭俊实际的,说明郭浚并不了解徐霞客“独上雁巅”之事。从诗的内容看,也证明,郭浚写的是徐霞客的台、雁之游。诗中写道:“今来复作台雁游,下榻同眠百尽楼,”这里清楚地表明,这首诗主要写徐霞客游天台、雁宕之事,是“复作台雁游”即第二次台雁游,与“独上雁巅”无关。因此,我认为,高峰先生误解了郭浚这首诗,它决不是写徐霞客“四上雁宕”,而是写徐霞客与徐仲昭一起第二次同游天台与雁宕之事。因此,以郭浚这首诗作为徐霞客“独上雁巅”的证据,岂不是张冠李戴,是不能成立的。
高峰先生在《侧身回望台雁峰——徐霞客四上雁宕考》一文中,证明徐霞客“独上雁巅”为“四上雁宕”的第二个证据也是错误的。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此外,丁文江先生认为《游记》与《墓志》所记,皆为‘三游雁宕’。”其实,仔细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游记》中“初四月,……过白云,云外二庐……又二里……溯水而上二里……又二里,逾山脊……北上二里,一脊平峙……余从东巅跻西巅,倏踯蹰声大起,则骇鹿数十头也。”《墓志》中,“上龙湫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冢也。再攀登往,上十数里,正德间白云、云外二僧团瓢尚在。又复二十里许立其巅,罡风逼人,有糜鹿数百群,夜绕于宿。”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高峰先生说;“丁文江先生认为《游记》与《墓志》所论,皆为三游雁宕。”丁文江先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是年三月为第二次”(见《徐霞客先生年谱》24页),即徐霞客第二次独游雁宕,怎么变成是“皆为三游雁宕”呢?这种把莫须有的“罪名”加给丁文江,是绝不应该的。二是,关于徐霞客“独上雁巅”是徐霞客四上雁宕的第三次,这一观点不是丁文江先生提出来的,是我在《徐霞客首游天台、雁宕之考辩》一文(见《徐学研究》2024年第四期)中首先提出的。高峰先生把我的这一发现权转给了丁文江,不知有何依据?因此,高峰先生硬是把《墓志》所记的徐霞客“独上雁巅”,和《游记》中徐霞客与徐仲昭一起“三游雁宕”,说成一回事,这是不恰当的。高峰先生所例举的《游记》和《墓志》中两段相互比较的文字,虽然文字中都说到了登上雁峰,而且见到了糜鹿,但丁文江先生没有把这两者混淆,也不能证明徐霞客“独上雁巅”,是他第四次上雁峰之证据。因此,我坚持认为,徐霞客“独上雁巅”,是他四上雁宕中的第三次,时间是在1630年的下半年。
四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徐霞客四游雁宕的时间和大致经历如下:徐霞客一游雁宕,是1612年,同游者云峰,时间在春夏之交;徐霞客二游雁宕,是1613年四月,同游者徐仲昭,还有莲舟上人。此次先游天台山,而后游了雁宕山,《游记》有《游雁宕山日记·浙江温州府》一文;徐霞客三游雁宕,是1630年下半年,这次是徐霞客单独游雁宕,在山顶见数百群糜鹿,具体记载见陈函辉《霞客徐先生墓志铭》;徐霞客四游雁宕,是1632年四月至五月,同游者徐仲昭。此次也是先游了天台山,而后游了雁宕山。见《游雁宕山日记后》。
由此可见,徐霞客四游雁宕中,“独造雁山绝顶”之游,是徐霞客唯一的一次单独上雁山绝顶之游,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陈函辉之所以把它在《霞客徐先生墓志铭》中单独叙写,这也就是他要引起人们关注,并把它从“四游雁宕”中区分开来的良苦用心所在!
2025年4月